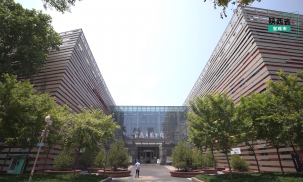开放时间: 2022-12-19至2022-12-31
开放时间: 2022-12-19至2022-12-31  活动地址:
活动地址: 收费信息:免费
收费信息:免费玉米在陕西的种植,最早起于陕南,继而发展到陕北,先是贫瘠的山区种植,后来才种植于稍好的土地。到了清代末期,关中始有“棉花进了关,玉米下了山”的农谚。陈仓人对玉米的叫法不一,贾村原一带群众称之为“番麦”或“番米”,西山群众则称为“籼麦”,川道统称玉米或玉麦。
《陕西省农业志》中关于马铃薯引进的记载与玉米有相似的经历。马铃薯的传入晚于玉米,大致在清初传入,而传入陕西则到了乾隆年间。清代陈宏谋的《培远堂文檄》中有一篇《劝民领种甘薯谕》记载:乾隆九年(1744),陕西盩厔县曾从河南觅种雇人,传习栽培。足见马铃薯作为食用农作物,其引进、推广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而作为主食则更晚一些。
究竟玉米和马铃薯的引进为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清以前的中国人口峰值大致在明朝万历年间(1600),大约为一亿九千万至两亿。经历了明末清初四十余年的频繁战争和瘟疫灾荒后,人口迅速恢复增长,乾隆五十五年(1790)人口突破三亿,道光十四年(1834)人口突破四亿,即四万万。是什么决定了人口的翻番,答案只有一个,粮食的多样性和粮食产量,马铃薯、玉米成为粮食增加的直接原因。
外来物种的引入,不仅使人口暴涨,经济也随之复苏,虢县镇上开始出现了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新奇消费品——洋烟。据《陕西省烟草志》记载,陕西烟草种植始于明末。清康熙(1662—1722)年间,在小农经济商品化进程加快的推动下,烟叶生产曾有较大发展,并在渭河、汉水及黄河沿岸交通、商业较发达的地方出现了小块集中产区。这种新物种也曾一度被朝廷所禁止,在乾隆五十年知县邓梦琴主持编纂的《宝鸡县志》中如是记载:服之而醉,名曰烟酒,今邑沿渭河一带皆蓺此而货焉。这种令人服之而醉、被称之为“烟酒”或“相思草”的神奇玩意屡禁不止且被课以税赋后,朝廷与烟民则各取便宜,听之任之了。另一种同样受宠的物种便是辣椒。辣椒在明代学者高濂的《遵生八笺》中被称之为番椒,与玉米(番米)、马铃薯(番薯)、西红柿(番茄)一样,其最初名称中少不得一个番字。辣椒出现之前虢镇同整个川陕地区调料中的椒均称木椒或花椒。辣椒的引入,极大刺激了人们的味觉,改变了食物品种。岐山臊子面的起源无疑不会早于清初。此前的臊子面可能是扶风的不含辣椒的臊子面,或者是农耕发源地武功的旗花面。
那么虢镇一带的粮食亩产究竟能达到多少呢?我们从史料中找到了答案。乾隆四年(1739年)五月十一日(6月16日),川陕总督鄂弥达、陕西巡抚张楷写给朝廷的奏折对关中地区丰年的粮食亩产可见一斑。“……差员于附近省城各农庄备细查验,每亩实收市斗麦一石三四斗至一石六七斗,合之仓斗每亩俱收麦二石以外。且所收之麦皆饱满光洁,每市斗可磨面十四五斤,较之常年每斗又多磨面一二斤。”按一市斗合三十斤测算,乾隆时期的小麦产量可达到三百九十斤至五百一十斤不止。(另有一种计量解释认为,每斗14.8市斤,每石十斗,则每石为148斤。文中每斗磨面十五斤显然并非以上计量算法。)
由这些地方督抚大员写给朝廷的奏折看,其对农事、气候的关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鄂弥达于乾隆六年(1741年)所写的奏折对清明前后的雨情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报告得细致透彻。“秦地农民全以夏麦为主,而夏麦之丰歉专视春雨之迟速。其年逾八九十之老农,每言清明前十日得雨便是十二分丰年,清明得雨便是十分丰年,清明后十日得雨,尚有八九分可望,惟至十日后竟无雨泽,乃为歉岁。”同年,陕西布政使帅念祖四月十九日(6月2日)的奏折写到“陕省地方全赖夏禾成熟。民间地亩种二麦者居十分之六,种豌豆者居十分之二,农家相传有三秋不及一夏之说,盖云三年秋禾之熟不及一岁夏禾之丰也。……现今节交夏令,大麦将次结实,小麦已经敛浆,豌豆正在扬花。”
地方官大多有报喜不报忧的习惯,对大有之年的粮食产量自然有虚报成分,而到了灾荒之年或夸大灾情增厚朝廷赈灾银两或瞒报灾情讨好上宪,全奈地方当政者好恶。关于川陕总督鄂弥达、陕西巡抚张楷给朝廷奏称的小麦产量,虚增产量板上钉钉。民国三十一年(1942),国民政府《陇海铁路沿线经济调查》记载,当年的小麦的平均亩产仅为一百〇三斤,即三市斗半。以乾隆年间的小麦品种而言,不及民国年间当属自然,故而不排除有乾隆间有四百斤的亩产,平均亩产则不会超过百斤。《陇海铁路沿线经济调查》中关于其他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及产量也为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粮食结构提供了依据。就种植面积而言,小麦最多,其次为大麦,其余依次为高粱、玉米、大豆、豌豆、谷子、糜子、荞麦等。以亩产论,高粱产量最高,均亩产二百二十市斤,玉米为一百六十市斤,大麦为一百四十八市斤,大豆一百一十八市斤。
另据虢镇四堡的老人回忆,虢镇周边亦有种植青稞者,很多人难以分辨青稞与大麦的区别,一概以大麦称之。